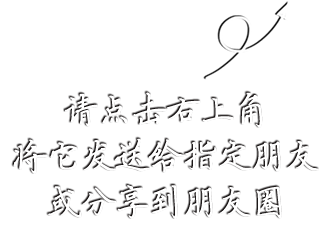德国法学中的法体系理论
《法学中的体系思维与体系概念:以德国私法为例(第2版)》序言节选
法治日报
2024年03月20日
□ 舒国滢
自21世纪初以来,法学方法论在我国法理论界渐成显学,个中原因诸多,但一定程度上与域外特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方法论论著经由译介而为我国学界所继受有关。不过,纵览近年来法学方法论领域对域外法学方法论论著的译介工作,虽有众多学者无私投入精力,但仍有相当多尚待改进的余地。一者,在纵向时间上,针对特定理论问题,往往无法对学术发展史上之重要文献进行完整译介,而是译者止步于片段式抽取译介,易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端。二者,在横向广度上,法学方法论诸多领域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专题性研究专著的译介,尚为一片空白,无力推动研究向深处全面发展。
此二问题,在法体系理论领域同样存在。自启蒙运动破除中世纪蒙昧禁锢,欧陆学者得以运用人类理性,历经迭代演进,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将自身对外在客体之认识,构建成逻辑自洽之公理体系,冠以科学之尊号,尤以数学为其代表。自此,“体系”与“科学”便紧密相连。而以人类自身之行为为规范对象的法学,亦孜孜不倦寻求分享这一殊荣。无论是“莱布尼茨-沃尔夫”时期的理性自然法学派,抑或普赫塔时期达到巅峰的概念法学派,都试图运用公理方法建构法律科学体系。此种极端的公理演绎体系,很快迎来自由法学派和利益法学派的猛烈抨击。主要由利益法学派代表人物黑克所提出的“内部体系—外部体系”的区分,虽被我国学者奉为圭臬,然而,对于20世纪以后体系理论的新近发展,却仅有零星介绍,更遑论对此宏大历史线条上的各具体发展阶段的详细译介。而在横向上,特别是对体系与法律适用和法律续造之关系、体系构建、体系断裂等相关具体问题,现有译介成果更是未能覆盖。
历史业已发生变化,我们应当把法体系理论置于当今整个思想的气候与氛围之中加以审查。应当看到:社会高度分化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随机决策、具身伦理与个体筹划,而强调宏大叙事、格式(一般)演绎与体系思维的传统经典科学在此过程中逐渐趋于式微,甚至走向“至暗时刻”。种种量子态表明,人们越想要在智性领域接近真相,越需要摆脱整体解释,甚至需要彻底拒斥实证科学的气质,遁入还原主义的轨路。这似乎意味着,知识可能不再绝对地来源于纯粹理性,更多地可能来自经验;普遍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逐渐沦为清算对象,多元因果和“选择性亲和”成为意识流等。如果说经典(自然)科学生产结构化的知识,那么,依据或类比这种规准建构的经典社会科学必然在认识论上承诺或采用“二级结构”。
规范科学的形态学标志开始瓦解,“体系”及其思维作业开始显得不那么重要:规范可以附着于争议与事件而产生和存在,解释可以屈从于主观与心性而成型和变化。前者有“判例法”作为倚仗,有“领域法”背书;后者有“能动主义”为矫饰,有“现实主义”(司法信任)而续造。虽然我们应当承认,这些观念并未将“体系”完全抹杀,但“体系”却仅在局部被矮化为某些操作工具,它不再是规范知识之生产方式,也不再为规范知识的自组织提供有益的效价。若秉承“存在即合理”表面语义所建构的那种粗糙真理观,则我们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地得出结论,至少在某个或某些法律地理(人类的法律视域)的观测内,抛弃“体系”并不是什么荒诞而无法想象的事情。如此一来,这个问题便成了过分棘手而又不得不找到答案的那个——“体系”对我们而言真的重要吗?
终极答案我们不得而知,这种对垒和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我们能清晰知道的是,英美法系传统中曾有过构建“体系”的深刻尝试:比如由杰弗里·吉尔伯特、杰里米·边沁、詹姆斯·斯蒂芬、塞缪尔·马奇·菲利普斯等接续建构的理性主义证据法传统,大陆法系传统中亦曾有过体系思维的悖逆构想:特奥多尔·菲韦格于1953年出版的成名作《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便是典型的例证。其在书中宣称,只有借助论题学思维,而非体系思维,才能正确把握法学的结构。倘若以“时空压缩”的逻辑建立思想实验,则是否意味着“体系”的零和之争已在欧陆(法学方法论)传统的纵向捭演中得到缓释或统合?然而,事实上,菲韦格的“异见”甫一问世,即遭到了体系思维支持者阵营的强烈阻击,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就是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他以教授资格报告为基础,于1969年出版了《法学中的体系思维与体系概念:以德国私法为例》一书,随即成为德国法学理论上系统讨论法体系问题的重要文献。该书第七章对菲韦格的论题学观点进行了原则性批判,最后也提出了“论题学尚存的可能性”。这是一本浓缩了法文化隔膜与体系思维合理性之争的重要著作。
卡纳里斯教授在其撰写的法学方法论著作中,从未止步于阐述纯粹抽象的法理学理论,而是一以贯之地追求部门法教义学和法理学理论的有机结合。恰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一样,其不断借助部门法教义学上之具体经典案例和争议问题,归纳、发展出自己的抽象的法理学理论,同时借助由此发展出来的理论反哺解决部门法问题。具备此种横跨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是很多德国法学大家之共同点。而在我国,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长期隔阂,甚至相互轻视。在此背景之下,卡纳里斯教授的此种研究范式,尤其值得中国法学界借鉴。
总之,本书是我国读者深入了解和研究德国法学中法体系理论所无法绕过的高地,必将在中国法学界激起同样的理论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