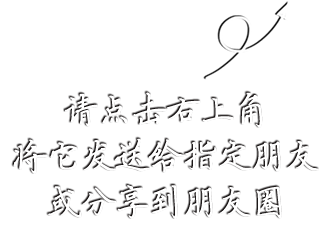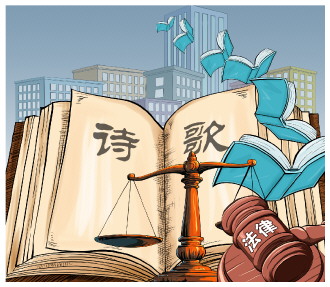陈锐
法律与诗歌似乎处于对立的两极。有人明确提出,“在法律领域,应拒绝诗歌”,更有人夸张地认为,若允许判决采用诗歌形式,一些法官会“为押韵而杀人”。法律与诗歌真的如此排斥?事实并非如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律与诗歌保持着密切关系。
法律与诗歌产生于同一张温床之上
古代有“诗法同源”之说。意大利学者维柯曾说,“古代法学全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得出了大致类似的观点,德国学者雅各布·格林发现,流行于北欧地区的古老法典都具有诗性特点,古代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法律同样充满诗意。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歌谣中也可见法律的影子。
古代的一些伟大诗人被奉为“未被世人承认的立法者”,维柯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东方的佐罗斯特、埃及的霍弥斯、希腊的奥辅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中国的孔夫子。或许还可以添上荷马的名字,因为“希腊人视他们的诗人为法律权威,荷马的诗歌和他们的法律卷册经常一起摆放在法庭的桌子上”。
近代时,法律与诗歌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另外的形式呈现,用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话说:“很多诗人是从法学院逃逸出去的学生。”很多拥有世界性声誉的诗人最初是学习法律的,如歌德、席勒、海涅、薄伽丘、彼特拉克、乔叟、莎士比亚、蒲柏、雪莱、泰戈尔等。很多较有名气的英国诗人曾是律师会馆的学徒,如托马斯·米德尔顿、约翰·马斯顿、威廉·布朗、沃尔特·司各特等。美国情况大致类似,华莱士·史蒂文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威廉·卡伦·布莱恩特曾在威廉姆斯学院学习法律,桂冠诗人埃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短暂地学过法律,之后逃离法学院。辛辛纳图斯·海涅年轻时曾担任地区法院法官,执业之余写下了大量描绘美国西部的诗歌,赢得了“西拉斯的诗人”之美誉等。
法律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法律为诗歌提供重要素材,诗歌则是表达法律的重要形式之一。自古以来,法律一直是诗歌的不竭主题。诗人们用诗歌赞颂良善的法律,讴歌公正的司法,诅咒恶法,批判不公正的司法,传达深刻的法哲学道理。
法律与诗歌在现代的疏离及其原因
到了现代,法律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复存在。用美国结构主义诗学倡导者乔纳森·卡勒的话形容,法律与诗歌之间产生了“围墙”。美国学者德文·拉金特夸张地认为,法律与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终结。用稍和缓的说法就是法律与诗歌在现代已开始疏离。具体表现在:很多法律期刊不再刊发法律诗歌,有关法律与诗歌的讨论大大减少,没有人像柯克大法官那样,用诗歌撰写法律报告。少数大胆的法官用诗歌撰写法律意见,会招致非议,甚至受到处分,一个经常引用的例子是“关于罗姆的调查案”。法官罗姆在撰写一件案子的判决书时,曾用诗歌解释判决理由,最后却受到了处分。州最高法院的解释是:“虽然法官有权用诗歌撰写判决书,但无权让诉讼当事人成为公众嘲笑或轻蔑的对象。”
法律与诗歌疏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造成法律与诗歌疏离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诗人和法学家都逐渐专业化,法律与诗歌开始出现分野。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分析道,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现代的法律逐渐由非理性、经验性的法律向着更系统化、更逻辑化的法律方向发展,法学教育逐渐由“技艺”转向“科学”,这使得法律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攀升,该趋势无形中加剧了法律与诗歌的疏离。此外,法律与诗歌的疏离还有其自身原因。现代法律讲究语言的规范性和明确性,追求真实性、客观性和统一性,而诗歌中充斥着隐喻和象征,其语词富于主观性、创造性、多义性,这使得法律与诗歌在语言风格上差异巨大。
当然,法律与诗歌疏离,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完全绝缘,只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般紧密,诗歌从法律事务的某些部分退了出来,或者说,在某些法律领域,原本常见的法律诗歌,现在已变得比较罕见了。
当代法律领域为何仍需要诗歌
很多有识之士指出,若法律与诗歌长久处于一种割裂状态,会引发诸多问题,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法律与诗歌的关系,了解诗歌能为法律做些什么。
首先,诗歌能软化法律语言,改变法律语言晦涩难懂的状况,消除群众与法律间的隔阂。虽然有法官因运用诗歌进行判决而受到处分,但仍有法官根据手头案件的特点,得当地运用诗歌,取得了较好效果。如一名法官用抑扬格形式,以野生松鼠的口吻描述了被人收养的痛苦经历:“我,一只松鼠,因为被人爱怜,来到这里,处于被囚禁状态,很多年来,我确实独立生活,住在一个没有恐惧的地方,可爱而多变的人儿,一直关心着我,我不用四处找寻橡子,因为橡子就在那里,我被人宠着、爱着,虚度着光阴,饥饿的记忆,不再属于我。但那不符合我的本性!我不过是野生动物,不是被宠着的孩子……”这种以诗歌形式发表法律意见的做法成功地说服了当事人。
其次,诗歌通常以精炼、富有节奏和韵律而著称,易于引起情感共鸣。美国民权活动家玛雅·安吉洛的自传体小诗《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就能唤起人们对“自由”的憧憬:“笼中的鸟儿唱着歌,带着恐惧的颤音,歌唱着未知事物,渴望自己的歌声能传到远方山丘,因为笼中的鸟儿在歌唱自由。自由的鸟儿畅想着微风,畅想着轻风吹拂的树木,畅想着黎明草坪上的肥美蚯蚓,并宣告天空属于它。但笼中的鸟儿站在梦想的坟墓上,它的影子在噩梦的尖叫中回响,它的翅膀被剪断,双脚被缚住,它张开喉咙歌唱。”
再次,诗歌可以为法律注入人文社会价值,弥补现代法律中人文社会价值之匮乏。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法律已经“异化”,法律中的人也被“异化”,用努斯鲍姆的话说,“个人甚至比不上一只可以被清晰计算的昆虫那样具有独特性”“个人的独立性、个人内心深处的希望、爱和恐惧被视而不见”,因此,在法律领域,强烈呼唤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回归,诗歌正好可以贡献力量。
最后,诗歌还可以在当代法学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诗人重视雕琢语言,立法者亦应如此;诗人喜用隐喻、夸张,这些手法在法庭辩论中同样重要,成为说服法官与听众的重要工具。此外,将诗歌当作一种教育工具,可以使学习过程变得更有吸引力,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背后的价值。正如阿克里伯尔德·麦克利士总结的那样:“诗歌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混乱生活,使困惑、愤怒的心能认识到一种秩序……若没有诗歌,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人性。”
总之,当代的法律领域呼唤诗歌。正如卡多佐的小诗:“诗歌无处不在,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它优雅地出现在书本上,在新闻里,在法律中,在肥皂剧内。它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它是我们的惊奇,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平凡日子。诗歌是意象的创造,是激情,是脚尖的节奏,是歌唱。法律中充斥着,反映人性的极端案件,等待干预,等待执行,就像诗歌等待评判一样……”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