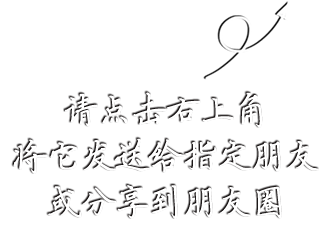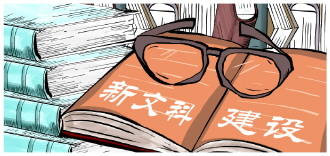关于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
法治日报
2025年04月09日
□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也面临许多新时代的新任务与新挑战。面对多面向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改革任务,应该用联系的观点去理解与回应。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二者不应当做割裂化的理解。遗憾的是,当下无论是针对新文科建设的讨论,还是针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都存在相互割裂的问题——在谈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会忽视新文科建设这一任务,在谈论新文科建设时又会忽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使命,尚未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将会导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呈现碎片化状态,无法进行体系化、系统化的建构。在我国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各自功能,实现二者的一体化推进。
无论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是新文科建设,都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展开讨论,这也是认识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视角。本体论视角是指研究存在和本原以及有关存在者的本质、分类及范畴的视角,主要讨论“自主知识体系”与“新文科”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视角是指研究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主要讨论“自主知识体系”“新文科”与社会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方法论视角是指认识、评价与改造世界的方法,主要讨论认识、评价与改造“自主知识体系”或“新文科”的方法。
第一,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或是新文科建设都面临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何谓“新文科”、何谓“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它们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基本原理是什么、基本范畴是什么?需要用具有通用性的方法进行讨论。以基本概念建构为例,新文科体系实现了“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的范式转型,矫正了精细化、专业化社会分工背景下对知识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不断消解,减少了专业之间、学科之间的知识壁垒以及知识本身的碎片化,弥合了学科之间的龃龉,形成了学科合力。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单一化、碎片化的学科知识结构已经难以回应与解决复杂的实践难题。这也就意味着,新文科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群不是叠加模式,而是融贯模式,需要从既有的学科体系中提炼概念内涵与外延,并经由科学方法融合为全新的、独立的概念,从而成为供给交叉学科独立运作的自主概念。同时,新文科背景下所建构的新概念也需要接受自主知识体系的检验,并将其纳入自主知识体系之中,丰富自主知识体系内部的概念体系层次。
第二,从认识论视角来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新文科建设都会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回应与解决,二者存在各自的问题域。以“问题导向”开展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基本原理的体现。那么,什么是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问题意识?首先,问题意识本身要关乎中国,以中国实践为起点,扎根中国大地,进而才能使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能够解读中国实践、阐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例如,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在中国的语境中仍然可以对一些传统的命题作出属于中国的回答,比如主权或人权问题、道德和法律问题、国家安全观与正义权利保护问题等;又如,在宪法学领域中关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理论建构的问题、关于腐败治理与监察法理论建构的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党内法规理论建构的问题,均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后在世界范围内需要呈现中国话语、中国视角、中国方案的问题。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中,这些问题既有中国的本土性,又包含与世界各国的关联性,哪些问题涉及理论变革与知识体系重塑、哪些问题又可以在传统理论中获得解答,都需要深入探究。其次,问题意识本身要打破学科壁垒,强调学科交叉,不局限于单一学科内部与单一知识域。新文科中的“新”强调的是以跨学科的视角思考问题,寻找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性与共同点;知识体系本身也因为体系特质而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具备知识融贯的基础,通过问题驱动知识结构重塑。最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新文科建设都进入共同的社会背景之中,需要深刻认识学科、理论知识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面临传统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能否检视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场景的检验。若割裂理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将会使理论失去生命力,难以指引实践发展。人类历史的演进经历了石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现代科技时代多个阶段。当下,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数字社会形态,新技术不断迭代,科技的高度创新与高度发展塑造着充满未知的未来。但是,现有的概念或理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社会共识尚未形成,传统具有支撑性的理论或概念失焦于社会实践之中。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需要回应数字社会这一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在数字时代,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某些情况下扮演着一定程度上的“准政府”角色,行使着“准公权力”。那么,能否用宪法学里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来分析相关现象,还是需要建构一套全新的理论?又如,关于数字时代的权利冲突规则,无论是传统的宪法理论还是部门法理论,都对权利冲突规则有着基本的理论建构,但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化趋势,新型权利不断衍生,传统的权利冲突理论能否回应?抑或需要建构新的权利冲突规则?再如,数字社会的运转虽然以技术为驱动核心,但是传统理论上的共识是不可忽视“人”的因素,要避免人的物化与异化,那么新的问题是人们有没有逃避数字的相关权利?人们有没有放弃和选择的权利?人们如何在可能存在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中保障自己的决策参与权?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传统理论的回应能力也有待检验。当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讨论新文科建设或者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走出传统理论的束缚,又会面临一些“无病呻吟”“假问题”“泡沫化”“虚假繁荣”“新瓶装旧酒”等争议。例如,数字人权问题在这几年形成了一批可观的成果,但是不少成果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是制造问题,共识性有限。到底什么是数字人权?究竟有没有数字人权这个概念?数字人权是人权在数字场域的表现还是全新的形态?这是数字时代人权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回应的问题。同时,在讨论数字人权的时候,数字人权与一般人格权的关系是什么?建构新概念时必须讨论其与传统概念之间是否具有相容性,要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新文科建设都面临如何进行知识生产的路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共同遵循的方法。首先,要准确把握好自主理论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要强调的就是“自主性”,新文科建设之新也在于破陈出新,以此为契机建构自主的文科体系,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在于摆脱国外学术话语对我国学术学科体系的不自觉影响,走出颇具时代特征的“洋泾浜语”,真正服务中国社会,并为全球发展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但是,在扁平化的世界面前,强调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新文科建设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走向关门主义、闭门造车的极端,仍然要博采众长,保持学科与知识体系的开放性,是要能够交流的、可供讨论的,但亦不可以用西方理论的议程设置标准来指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如学者所言,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有在中国的问题,也要研究属于中国的问题,还要研究中国在世界的问题。其次,要准确把握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知识生产同样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非单纯的逻辑思维过程,也存在政治与科学的内在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新文科建设都肩负着特定政治意义上的使命——打破知识生产国际分工中的知识霸权。因此,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知识体系建构,都需要自觉阐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