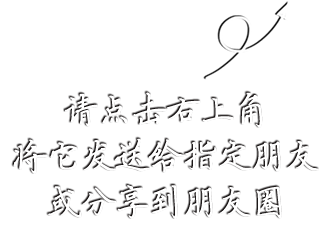构建数据权利体系
《数据权属论》引言节选
法治日报
2025年05月21日
□ 包晓丽
数据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而是抽象的事实概念。它是对事实、概念或指令进行数字化记录并处理的结果。数据和信息在各国法律文件中常常被混用,但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信息是数据承载的内容。数据具有载体性,必须借助于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为载体;数据具有代码性,数据的利用和流动都需要通过代码指令的方式实现;数据具有非排他性,它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数据还具有非消耗性,对数据的使用并不会减少其本身的价值,往往还能产生更大的福利价值。随着数据资产变得日益重要,研究数据权属的目的在于给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公平分配和行为激励的制度机制,以促进数据产业的有序和繁荣发展。
通过对数据生产过程和应用场景展开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数据在如下两方面与以有体物构建的财产权体系存在重大差别:一方面,数据的生产是用户和平台持续深度合作,共同投入和维系的结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人人共享”成为新的时代精神。数据的生产过程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商在一端、顾客在另一端”的管道式服务合同,在此过程中各方均同时扮演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用户数据是新型生产力来源。即使在封闭式数据平台中,数据作为用户消费行为的正外部性溢出,它也是价值产生的重要原材料,这也是为何中央文件明确肯定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此外,数据应用场景的内容取决于人们的想象力和技术可能性,数据服务合同的内容也丧失了经典交易原型中的模块化和确定化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变化性和合同的不完全性。
另一方面,数据同时承载了不同主体多样化的利益期待,它是包含了公共利益、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开放的权益集合。数据权利束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物上所有权概念。由于法律概念是对社会生活的抽象和总结,当观察的对象由工业时代的有体物转变为数字时代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所有权只是财产权谱系中的一个类型,从公共物到权利最圆满的所有权,财产权的形态表现出由简及繁的特征。而数据权利恰恰处于该频谱的中间部分,表现出合作性和有限共享性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以“数据权属”为题并不代表肯定了一个单方的、排他的、绝对的数据权利归属,而是遵循了既有法律制度用“权属”这个概念描述权利安排和分配方案的表达习惯。
通过对数据合作生产过程的描述和对数据背后权利哲学与权属分配的社会效应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数据权属的分配并非简单归属于某一方的问题,而应当结合数据的具体类型,在对利益期待的重要性和各方贡献值予以测量的基础上,判断利益实现的先后顺序。具体而言,对于与人格利益有关的数据,如果用户和平台在标准化的数据服务合同中就数据权属作出明确约定的,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对私权利的自由安排,但隐私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在此列。当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无效时,用户隐私保护和积极利用社会关系链数据等诉求构成用户重大利益期待,应当得到优先满足。但用户应当通过支付隐性对价或者显性对价的方式,对平台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合理补偿。对于与人格利益无关的数据,数据企业在数据增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根据具体贡献程度分享数据收益。
在数据资源价值流通方面,数据的非排他性与非消耗性为流通与共享提供了技术可能。与此同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数据收集与共享行为同样引发了隐私泄露、数据独裁的风险与担忧。在网络借贷法律关系中,授信机构依据平台提供的信用评价作出信贷决策,而该分析结果又以平台及其关联企业和外部机构间的广泛数据共享为基础,涉及主体众多。在此情形下,知情同意规则存在被架空的风险,用户信用利益存在遭受隐蔽侵害的可能,“超级平台”还将产生数据垄断和算法歧视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从强化数据主体权利、明确网络借贷平台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两方面入手,构建公平、有序、健康的数据共享生态体系。
任何权利框架都并非空中楼阁,而需要具体制度规则的支撑。构建数据权利体系的最后一个步骤即在法律规则上对其予以妥当安排。实际上,数据权利的财产权保护和侵权法保护并非二者必居其一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财产权保护有利于加强当事人对数据的控制、鼓励交易的自由协商,但是也有“敲竹杠”、阻碍数尽其用的风险;侵权法保护正好相反。就数据权利规则的规范类型而言,由于数据是一宗开放的权利束,其中的人格权益是与用户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密不可分的,是用户不可让渡的权利,与此对应的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而财产利益的分配规则是一项任意性规范,对双方的意思表示起补充解释作用。除非用户能够证明该格式条款具有法定无效的原因,或者数据中还承载了用户的人格权益(如继承),否则法院不宜否定平台政策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