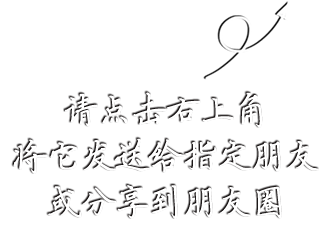国家的事 我尽了我的职责
《当代中国民法典编纂研究》序言
法治日报
2023年03月22日
□ 梁慧星
我1962年考上西政,所学习的专业课程中只有宪法学和婚姻法学有正式教材。作为专业基础课的民法学,已经改名为“民事政策学”,刑法学改名为“刑事政策学”。薄薄的两个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的一个小国企。直到1978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法学专业,仅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单位招生,我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当时民法学专业就招了两个研究生,另外一位同学后来做了律师。
1985年开始起草民法通则。佟柔、江平、王家福和魏振瀛四位教授作为立法机关的咨询专家,后来被称为“民法四先生”。这四位老师把草案拿回本单位讨论,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民法通则在1986年获得通过。1987年修改经济合同法,我加入了修改小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参与了几个重要的立法,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同法的制定。
1978年,我成为王家福先生的研究生,是最早研究合同法的,我的硕士论文是合同制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合同法。我先后参与撰写了合同法、民法债权等著述,这为后来合同法的起草提供了理论基础。
1998年10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由我来报告物权法的立法方案。我报告完以后,王利明教授说,我不赞成梁慧星教授的意见。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财产特殊保护。我的想法是平等保护原则,一体保护。物权法草案在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区分所有制作为标准。在这个草案上,没有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王利明教授提出要严格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叫国家财产特殊保护。
学术界争论愈演愈烈,概括为三分法还是一元论的争论也是非常厉害,直到2004年、2005年,学界慢慢统一。概括为三分法,但是不再特殊保护。因此,虽然不是一元论,但是原则基本上是一样了。2005年,经审议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后没有料到出现了社会上的剧烈争论。
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发生了两个严重社会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个是两极分化的扩大。
正是这两大社会问题,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动摇,抓住物权法草案公布征求意见这个机会,指责物权法草案。所谓“违宪”、所谓背离社会主义、所谓搞私有化,其实质是挑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对继续改革开放。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分赴各省,给人大代表每人发一份草案,给予讲解。
民法学界也召开了一些会议,驳斥某些人对物权法的指责。但我们民法学者大多不善于论战,太过于书生气了。学术讨论要讲道理,而论战是不讲道理的,而是讲事实。因为各有各的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事实只有一个,是明摆着的。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民法学界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来自意识形态的考验。没有动摇,没有分裂。
民法学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就是制定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民法典。只有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已达到她的高峰。这是我的老师谢怀栻先生去世之前所讲的。
1990年是民法通则颁布五周年,当时某刊物发表了一期文章,批判民法通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之后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讲到中国制定民法典这个目标不能放弃。我申请成立了一个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从国家社科基金处获得了6万元的资助,完成了一个草案,1900多条,共9卷,约400万字。这个草案我做了20年,于2013年完成。2010年,我的眼睛黄斑穿孔,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看书就很困难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在统稿。草案后来出版了,也翻译到了国外。
199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找了我们几位民法学者开会说:“这届期满我就要退休了,退休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他在内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定了9个人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就叫“民事立法研究小组”。
20年过去了,这个小组的9个人,王家福不在了,王保树不在了,魏振瀛不在了,魏耀荣不在了,一多半都不在了。国家的事,我尽了我的职责。我最担心的是将来子孙后代说,别人不懂,你懂,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但你不敢说。留给后人说短长。